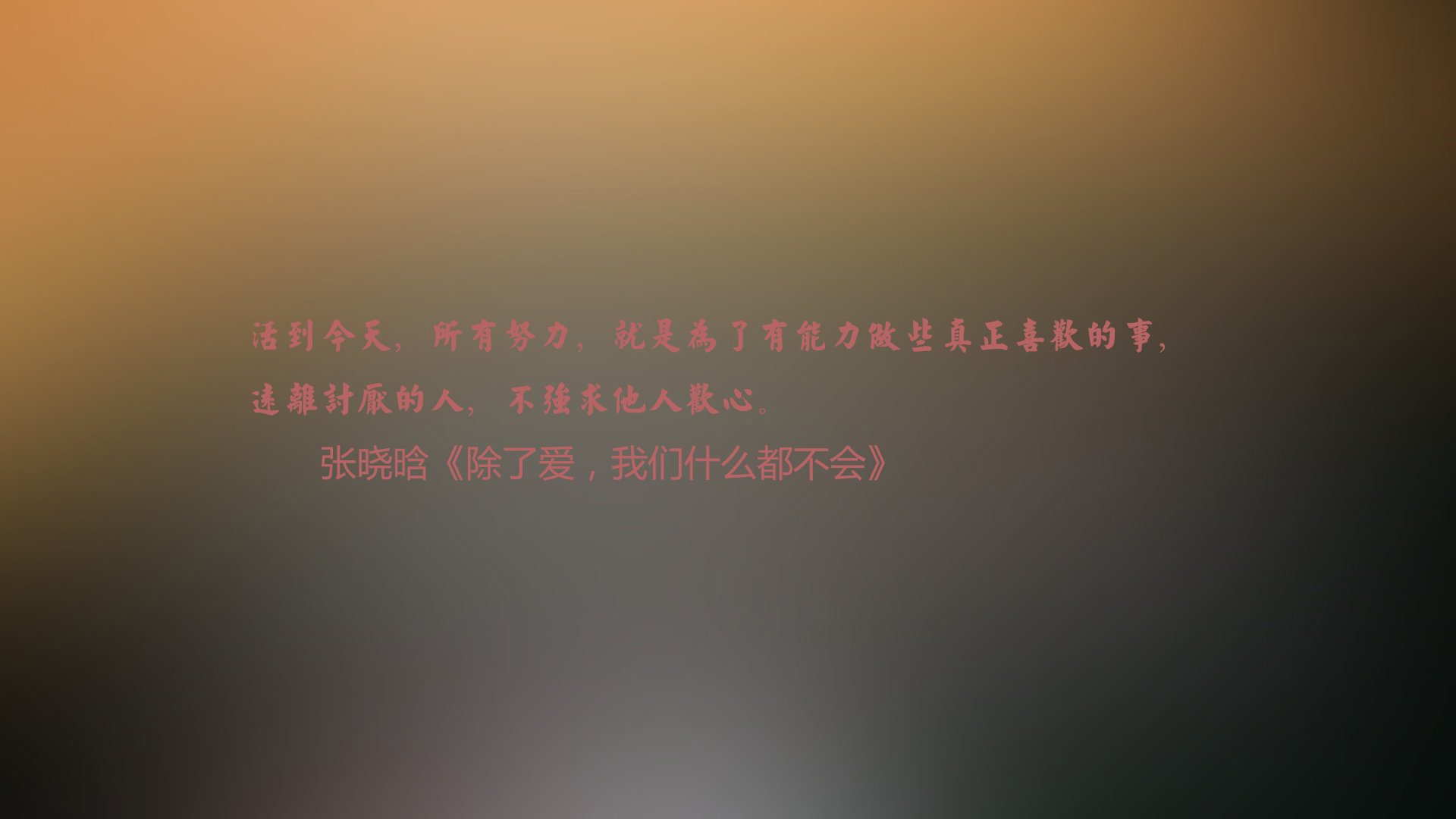瓜果物语
- 文化
- 3天前
- 279
□黄仕忠
小时候在山村里,物资匮乏,吃不饱,穿不暖。大人没得时间,孩子无人照管,一到放学,成群结队,大的拖着小的,小的跟着大的,讨世界(闯祸),扮家家,摘野果,拔山笋,办猪草,挖泥鳅,摸螺蛳,照黄鳝……漫山遍野,上蹿下跳;溪边水潭,“浪里白条”。少年不识愁滋味,留下无数美好的瞬间。
樱桃赶上先
儿时有童谣:“板柞扳过年,樱桃赶上先。”
板柞是一种拇指粗的水果,非常酸涩,又十分提神,酸尽甘回时,滋味悠长。它在过年前已结了果,但成熟得极慢,以至被春天里才开花的樱桃赶在前面。
小时候,我并没有吃过樱桃,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但念着这童谣,似乎又能感受很多层的意思。俗语说:“先赢勿是赢,后赢连赢赢。”先得的,不一定就先赢的,那么似乎是在鼓励后进应当发奋追赶。但也似乎在说:一切都是注定的,你哪怕先结下果子,也比不上后来者反而居上位——童谣最有意味之处,便在于这无穷的回味和多向的生发。
罗汉豆
罗汉豆,也叫胡豆、蚕豆,是从西域传来的品种。它的根茎上长有根瘤菌,能够自行吸收氮肥,收割了还能肥地,所以生产队种植很多。同时它又是最不占土地的,冬天时在田塍边用削尖的木棍钻一个孔,放进豆子,春天就可以长成一长溜茂盛的豆丛了。
孟春时分,豆子长到两尺来高,就开花了。那花是粉色的,带着黑眼,很像是一只只蝴蝶。之后麦子尚未成熟,豆荚却已长得很饱满了。青青的,鼓鼓的,比大拇指还粗,很匀称,皮很脆,剥开后,豆板已经成形,一荚里有两三个豆子,放进嘴里,满满的青香。大了,老了之后,豆荚长成一头大一头小,像“老虎板子”的那样。
小学生们放了学,走过路过,不动声色地顺手摘走一荚,单手两指一掐,剥开取出豆板,扔到嘴里。更淘气的孩子,躺在罗汉豆地里,摘下,剥吃,满地狼藉。这时的嫩豆板最是好吃,等长老了,就会有生腥味。但这样吃也最是浪费,如果被大人看到了,就会挨骂甚至挨揍。
豆子长成熟了,肉厚实了,可以煮来吃,吃时吐掉皮,也可以连皮吃。若是加上茴香、八角、盐煮过,阴干,就做成了茴香豆,就是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的那种。
再之后,豆子老了,收下,晒干,收藏。吃的时候,先泡在水中,待泡软后,再剥去皮。这泡软的豆板可单炒,可油炸,是喝黄酒的极好配菜,也可加其他肉蔬炒成菜。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这罗汉豆主要是作为“坚果”享用的。把晒干的老豆子在镬内炒焦炒熟,外焦内熟。炒成后的豆板异常坚硬,最是考验牙齿。孩子们牙口好,嘎嘣嘎嘣的,十分得劲。牙齿不够好的,就在嘴里多含一会,让口水泡软了豆板,于是香气与滋味并至。据说现在的孩子牙不太好,便是从小没有经受咬硬豆板这类锻炼的缘故。
还有一种做法,是先将豆子泡水发芽,待其破开豆皮萌出芽角时,再晒干炒熟,就不是那么硬了,而且有了回甘。
不过,这罗汉豆不能多吃,因为肚子里容易胀气。有童谣说:“罗汉豆两块板,放屁像敲册板。”
男孩子调皮,故意走到人前,一步一响;女孩子矜持,就只好少吃这豆子了。
六谷蔀
古人说到丰收,叫做“五谷丰登”。这玉米是从番邦引进的,位居第六,所以我们诸暨乡下叫做“六谷”,结出的棒子就叫做“六谷蔀”。
六谷通常是与番薯套种的。五月五,种六谷;六月六,插番薯。七八月里斩六谷,薯藤满地绿油油。单种的玉米则要晚一些,待到竿枯叶白,便已经是霜降时分。
六谷产量不低,自留地所种,可以代替一段时间的稻米。老六谷磨成粉,可作六谷糊,若是加入老南瓜,甜甜的糊羹,很受孩子们的喜爱。
要是做成六谷饼,就难吃了,就像北方“窝窝头”的味道。
那年头里山人的生活艰难,连玉米糊也是掺了许多杂物的,所以1978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去吉竹坑买树时,那家七岁的小女孩为能吃上“秃六谷糊”(纯玉米糊)而欢欣雀跃。
孩子们最爱的是嫩六谷蔀,就是现在菜市场常见带壳的嫰玉米,最好吃。其实只能讨个好味,不顶饥,家里通常留一两垄供孩子们尝尝鲜,煮的时候并不多。那时的品种一般,玉米棒上长得断断续续的,留着空缺,称之为“癞头六谷”。
当缨子从嫩白色、嫩黄色慢慢变成棕红色,又接近深褐色或棕黑色时,就可以掰嫩玉米煮来吃了。掰取后,其竿青中带棕,用勾刀斫下,取其下半部二尺左右,削去叶片,叫做“六谷梗(音guang)”,这便是我们的“青皮甘蔗”了。用嘴从根部咬开,用力一撕,扯下一长条皮,三下两个,用力咬断咀嚼,有丝丝甜味浸出。到杆梢头则内中呈絮状而无汁了。回想孩提时啃的样子,大约与熊猫吃竹子差不多。
老玉米可以煨来吃。我们偶尔也把六谷蔀放到火囱里,借柴火灰煨成焦裂,味道甚佳。
最期待的是“弹六谷大王”(爆玉米),爆过的颗粒膨胀起来,变得胖乎乎的,所以叫“六谷胖”。冬天下雨时,有“六谷大王佬”到村里来“弹”。通常是五分钱一次。如果加了“糖精”,就要一角钱。
最刺激的是爆开那一刹那,又想掩耳朵又不想掩,那“呯”的一声,从黑麻袋冒出了青烟,总觉得像是变戏法,小小的玉米,膨胀了好几倍,甜甜的,脆脆的,我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好像这是世界上凭空多出来的食物。
那时可“弹”的东西还有很多,有年糕片、黄豆、大米等等。
我那时候想:要是所有粮食都能这么“弹”一下,一下子胀出几倍,那么,我们就每天都能吃饱肚子了吧?
番薯糖
番薯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是食物,也是“水果”。
谚曰:“八月半,番薯芋艿搂搂看。”这“搂搂看”,是用一两根手指,或是用小巧的工具,试着搂挖一下的意思。中秋时分,番薯、芋艿都已结出茎块,可以试着挖来尝鲜了。但农人不会整株拔起或掘出,只掏取块头稍大的那个,让其余的继续生长。
孩子们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每天上学、放学路过,见那番薯根部的泥土微微隆起,裂开了细缝,便知有货。悄悄扒开挖出,搂出大拇指粗细的番薯,捋去泥沙,撩几根茅草擦一擦,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口中,于是“清香与甘甜同至,喘声并脆爽齐鸣”,可见吃时之迫切也。
“番薯糖”不是糖,是番薯干的一种,也是我家过年时最重要的“炒货”。它是待到霜降时番薯全面收掘后才安排做的。经过隆冬严寒,番薯中的淀粉开始转化为糖分,甜味渐厚。
选取那些大块头番薯,挑甜软些的品种,外形长歪、开裂倒是无妨。清水洗净,去皮,去圬眼,切成大厚片,放适量水,放到大锅内煮。待水干则薯已熟,撒上切成细末的橘子皮,连同薯块搅成糊状,撒一大把芝麻,再搅拌均匀,便做好了备料。
我母亲拿出洗得干净的旧饼干盒,底面朝上,盖一块洗净的湿纱布(有时是大手巾),四周下垂有余,然后舀一勺薯糊放于纱上,用薄刀(菜刀)用力抹散抹平压实,去其多余,然后提起纱布两端,放到竹编的晒箕里,轻轻取下纱布,就完成了塑形制作。
这样一次又一次,薄薄的薯饼,排列成行,晾在晒箕里。用的是圆盒,饼就是圆的;用的是方盒,饼便是方的。饼干盒底的深度,恰是薯饼的厚度,大约与千层糕一层厚薄相仿。
晾晒后的薯饼,结实坚韧,灰亮有泽,似乎隐隐可透见亮光。接着用薄刀切成长两寸、宽半分的小方条,再晒成干,这番薯糖的制作就完成了。然后置放于甏瓮之中,装满揿实,口上用牛皮纸或者笋壳包起,用细麻线扎紧,便能存放多时。
过年时,先将清水滩上筛选来的溪沙在镬里炒得热烫,再放入番薯糖,让砂子均匀地传导热量,番薯片先是发软,然后转为嫩黄,再转为蟹壳般的红黄,便是炒熟了。用漏勺捞出,犹是绵软,冷却片刻,变得硬朗,咬嚼时爽脆有声,橘皮的清香,薯糖的余甘,夹着芝麻的醇厚,余味不尽。
小时候,在冬天里,在春雨中,饥火难耐之时,便翻甏倒瓮,在屋子里搜寻可吃的东西,无论母亲怎么藏,我都能找出来。那第一要找的,便是这番薯糖。
家中拢共十几二十个瓮甏,排除伸手可及之处,不外乎钿橱顶端、衣柜之上,再就是重叠之瓮。往往十拿九稳。心想着只捏一小撮就盖回去,可经不起五次三番,最后就只剩下松垮垮的半甏了,令母亲开坛时哭笑不得。她不知道是我哥还是我,还是两个都是,只好嗔一声:“格两个阿兴阿黄!”
——现在我略以搜访资料见长,多少是因为从小就接受了这寻找食物“训练”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