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从来没有见过岳母娘如此激动!2012年初秋(即岳母说
- 社会
- 2年前
- 144
钱新华
岳母走时,很急,很突然,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人猝不及防。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约莫下午三点多,我接到内弟的一个电话。他一改往日平静的语气,急促而沉重地说:老妈妈胸部突发绞痛,并有呕吐、头晕的症状。我在电话中第一反应,就是急切地催他快找车送县医院。旋即,我从家里推出摩托车,直奔医院。
急诊室医生在心电图检查单子上扫视了一遍后,以毫无商量的口气下达了“紧急转往安庆市立医院”的通知。坐在医生对面的老人家一听,马上以抵触的口吻回敬医生:“这点病还非要跑到安庆?上次来不是只挂了几天水就好着……”医生只好小心翼翼地向她解释着:“这次不一样,需要做介入。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设备,做不了。”我和内弟也附和着医生的话,准备找车子转到安庆治疗。没想到老人家的情绪反而激动起来:“不能治就回家,就算死了也要死在家里!”唉,我从来没有见过岳母娘如此激动!这也难怪她呀,她是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病痛折磨的哦。十多年前,她急性阑尾炎发作,疼痛不止,我接到岳母娘邻居的电话,紧急赶到现场,背起她一肩跑到石矶头医院,及时做了手术。第二天下午,内弟从外地赶回调换了我,不到三天,就能下地活动。
2012年初秋(即岳母说的上次)的一天中午,我刚从田地里劳作回家,岳母(堂)侄媳妇的一个告急电话把我召了过去。一进门,就见老人家瘫坐在一把旧椅子上,脸色苍白,喘着粗气,高烧不止……我凑近跟前,弯下腰正准备背她去医院,可她就是不肯。从她表情和语气中,我可以看出她是在心痛我背不了。我只好把她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搀着她来到社区医院。院长接诊后,无奈地摇摇头,一个劲地催着:“快,快转院!”
当我带着老人家在县医院完成了心电图、CT等项目检查,再到住院部安顿下来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正在陪读的内弟媳闻讯,从会宫中学赶来替换了我。治疗了一周,就恢复出院。这次看来,老人家真是大限将至。此刻,我和内弟都陷入到了非常无奈、非常无助之中,只得违心地按她的意思去做。内弟招呼来了一辆的士,我推出了车棚里摩托。岳母娘临上车时,仍不放心地向我叮嘱着:“大姑爷(她向来都是这样以自己孙子的口吻称呼着我),你骑车子慢点些!”谁知这竟是她老人家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当我车子离家还有一段路时,就听内弟在电话里哽咽着:“老娘快不行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车笼头扶手顷刻间不再听我的驾驭,面前道路上瞬间飘起了一道道翻飞的黑影,我泪眼婆娑……是日,岳母娘伴随着西斜的夕阳,艰难地走完了她那七十八载坎坷人生路。
岳母娘的一生,可谓多舛多难。童年,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的骨肉分离。由安庆西门外海口洲被抱到枞阳石矶头当童养媳。成年,遭遇了未婚夫与养母双双腿子残废的窘境,以弱柔之肩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此时,她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即两种选择:一是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一穷二白的家庭,另嫁心仪人家;二是留下来与长自己十多岁且双腿残疾的男人成家,继续过着没有尽头的苦日子。然而,岳母娘选择了后者。她不忍心抛弃这个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穷家。周边的众乡邻每当提及此事,无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多年来特别敬畏岳母娘的主要原因。其实,人生就是在一次次选择中走过来的。而岳母娘的这种选择,我倒觉得也是一种智慧。她在做出这种惊人举动之前,恐怕内心深处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而复杂的心理碰撞。有句流行语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岳母娘正是选择了“口碑”,放弃了“金杯银杯”,才赢得了邻里的赞誉,下人的敬重。
岳母不识字,但她通情达理,凡事能看得开,想得远,岁月锻炼了她超人的毅力,生活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在“三年自然灾害”与“十年文革”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岳母娘与身体基本瘫痪的岳父相濡以沫,上要服侍失去自理能力的老婆婆,下要拉扯着四个未成年子女,中间还要伺候行动不便的丈夫。面对此情此景,我无法想象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含笑辞世,享年七十有三。老太太生前可没少夸岳母贤良淑德。
岳父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初。岳父是个急性子人,看着自己正值壮年,却成了“吃闲饭”的人,心里难免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苦闷,遂选择了以酒浇愁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凄苦。久而久之,在以酒浇愁愁更愁中浇上了酒瘾。到了晚年,嗜酒如命,长年累月,每日必饮。尽管家境艰难,岳母还是想方设法满足了岳父每天的酒瘾,直到逝世。岳父也可以说是“含笑酒泉”了。这绝对不是一般平常人所能做得到的。
我妻子作为岳母家中的老大,老人家为之付出心血更是难以言表。在那个“凭工分,称口粮”的年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实在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里除了省吃俭用,还得付出超过常人多少倍的含辛菇苦?
改革开放初,土地承包分到户,田园成了条纹布。农户的土地亩数虽不多,可土地块数不少,每日做农活,恰似在不同地块间“跑快递”。面对这种家中缺劳,且土地零碎分散的状况,正在读初中的内弟被迫辍学协助岳母种地。内弟底下两个妹子都还是在校儿童,帮不了任何忙,家中顶梁柱仍是岳母娘,她身上依旧压着没完没了的农活与繁琐的家务。
记得那时种地是这番情景:广袤的田园被切成了一块块薯片,阡陌纵横的稻田中见不到一根电线,微型电水泵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水稻灌溉,仍在使用那种从老祖宗手里传下来的人力水车。这水车越陈旧越笨重,弄上肩膀,一个壮劳力也得费不少气力。一当遇到风暴,人扛着水车行走,如同醉汉在原地舞步。试想一位柔弱的妇人是多么艰难?岳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她像贫瘠土地上生长的菅草,虽屡经风吹雨打,但仍然倔强地生存着。我的岳母,我的娘,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啊?
岳母娘一直有晕车的毛病,平时出行都靠两条腿量。到达最远的地方也只是安庆这个“大城市”了。因为那是岳母娘的出生地,那儿有她牵肠挂肚的年逾九旬老老娘和几位古稀的老姊妹。每去一趟,一路上总是天昏地转,呕吐不息,倍受折磨,然骨肉之亲,同胞之情,是任何艰难困苦所阻挡不了的。
199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在村任职的妻子骑着自行车去镇里开会,途中不慎被一辆私人合伙的大巴车刮伤,住进了县医院。岳母娘得知后,寝食不安,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硬是以步代车,足足走了几个时辰,在翌日天明,才赶到了县医院。我们见她一脸疲惫,既心痛,又想责备她几句,可是埋怨的话到了嘴边,还是被咽了下去,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内弟成家添子,两个妻妹也分别婚嫁有了自己的家庭。晚年的岳母娘虽不能从事重活,但勤劳的习惯早已深深地植入她的骨殖里。一年到头,总是闲不住,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四季瓜果、各种秧子,有如现代生产流水线上的商品源源不断。刚结出来的新鲜果蔬她总是舍不得吃,都拿到市场上去卖。她认为这些新上市的东西能卖个好价钱,很是划算。这就是岳母娘的秉性。其实也只是换回一些小钱,聊胜于无。
老人家去世前几年,两眼因白内障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平日里,在给果蔬秧苗拔草时岳母,常常误将菜秧苗当作杂草拔掉。我们本想通过手术复明,但经医生检查,因有高血压及心肌上的多种毛病,只能依靠滴眼液维持现状。在视网膜几乎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亮下,仍不断地培育着各种季节性菜秧子到街头去卖。这时,能来买她秧子的大都是她多年的老主顾。秧子由人家自行挑好,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钱。
晚年的岳母娘,基本上是一个人留守在家。内弟夫妇与两个姨妹夫妇都长年在外务工,孙子也上了大学,平时也只能在电话里与老人家说上几句话。我在退休前几年,每周也只是匆忙地去看望一两次,叮嘱她应该注意事项。我想接她来家里长住,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辞。我根据她有喜爱吃鱼的习惯,每次去也只是顺手买一小碗鱼给她煮煮。可她好面子,一小碗鱼儿明明完全可以在家中收拾好,而老人家每次偏偏拎着鱼到池塘边人多的地方去收拾,逢人便讲:“这是我大女婿刚送来的。”故而,我被滥得了“孝敬老人”的虚名。事后想起来,心里很是不安与愧疚。
岳母娘在世时,非常注重她的人情。每次来我家里,两只手上总是拎着大一包小一包,里面装的全是我小孙子与妻子爱吃的各种食品。她来一回,我们总要吃上好几天。
我和妻子的生日,她每年总是记得提前置办了礼物送来。为此没少被我们责备,而她那种任性的做法,也是任何人不能改变得了的,她总是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说法与理由。
如今,岳母娘走了岳母,她走进了墙上那个长方形的玻璃框里,永远地住在那里。她的目光依然还是那么慈祥,神态依然还是那么平静,面容依然还是那么随和,只是不再说话了……我想:她实在是太累了。
岳母啊,岳母,您,就是我的老亲娘。愿下辈子有缘,您老还是我的岳母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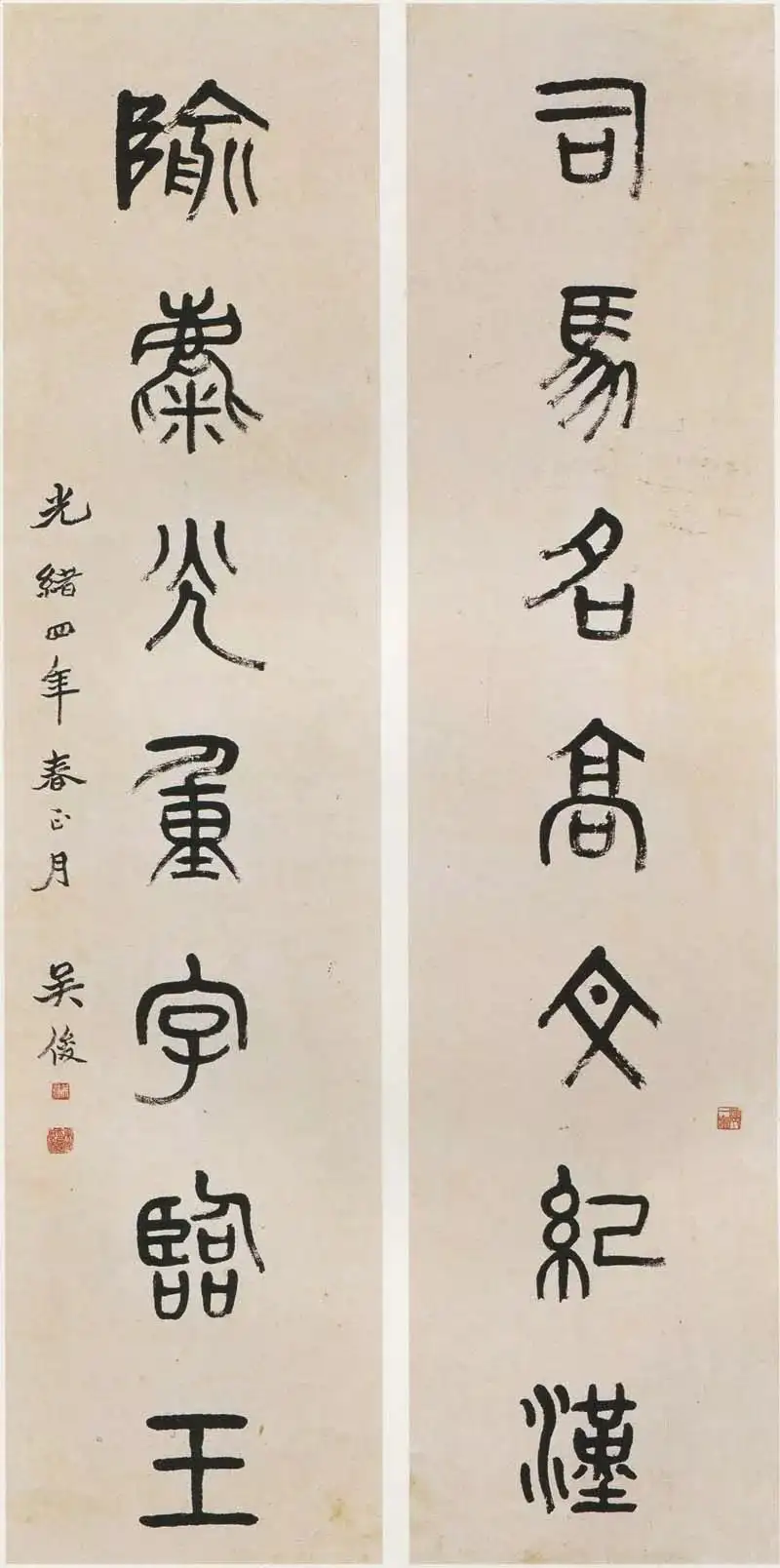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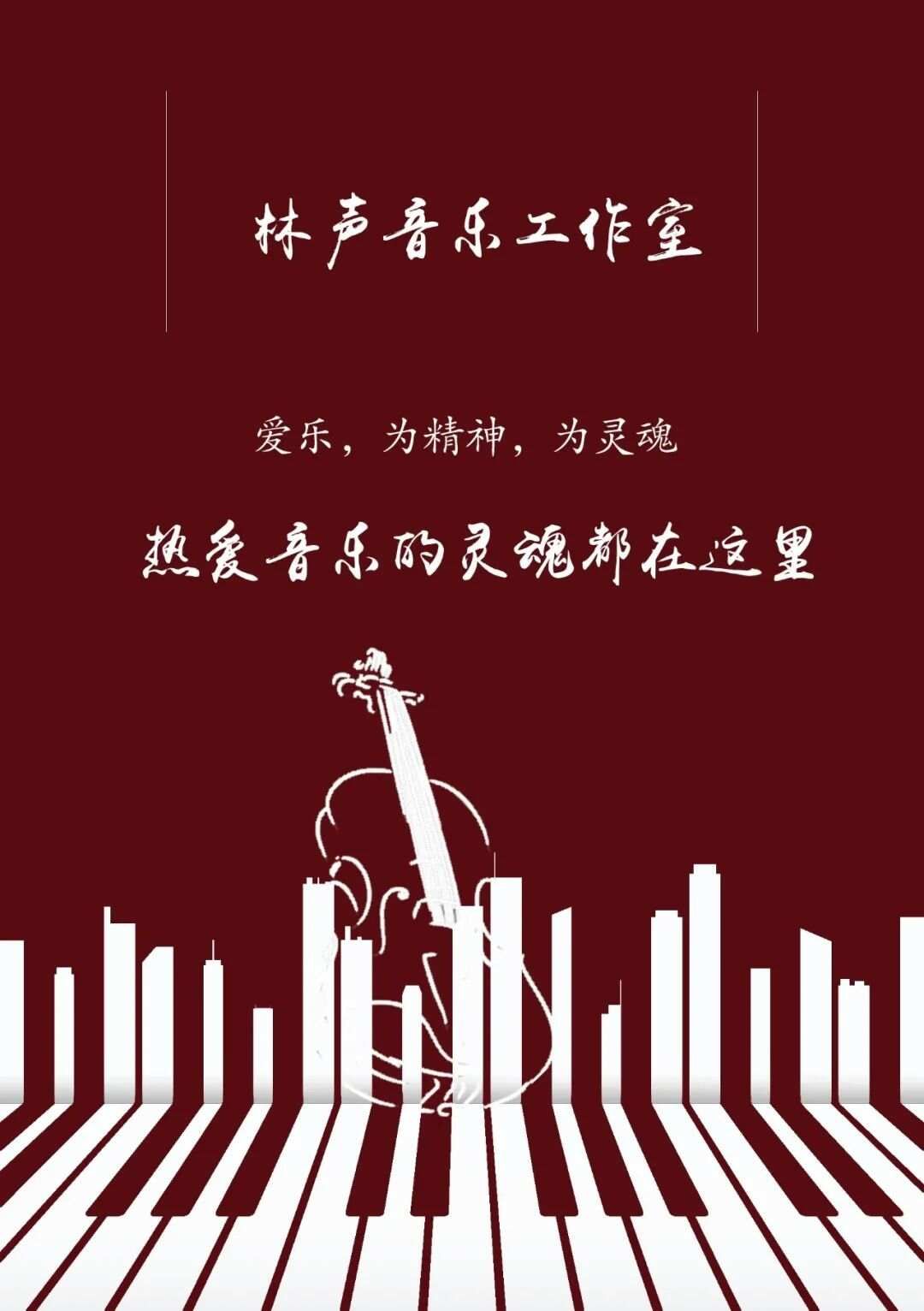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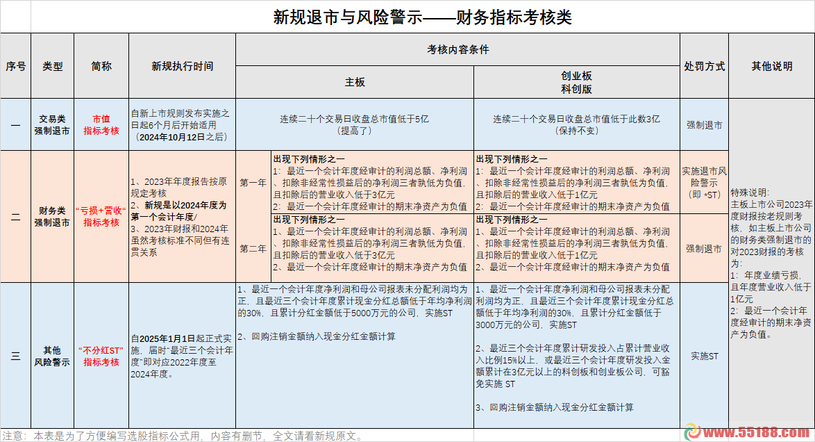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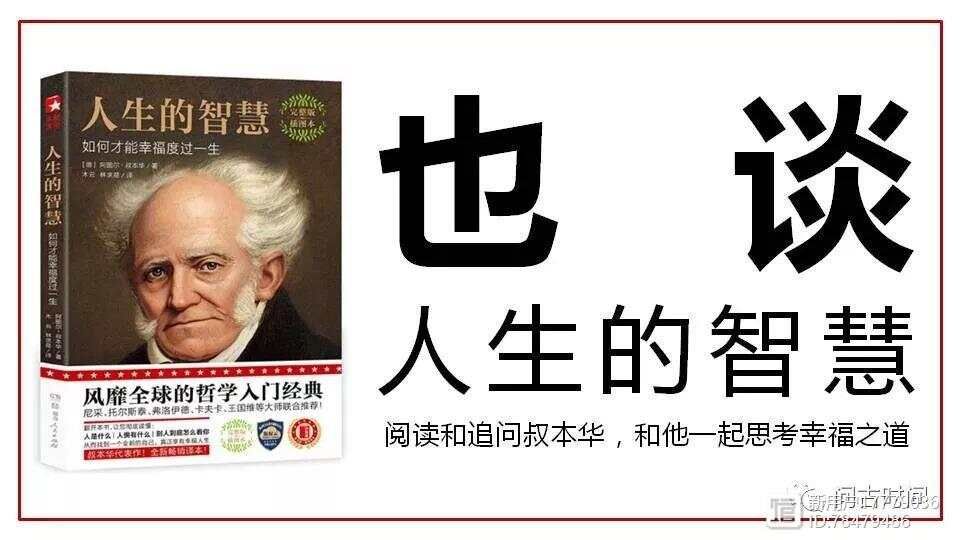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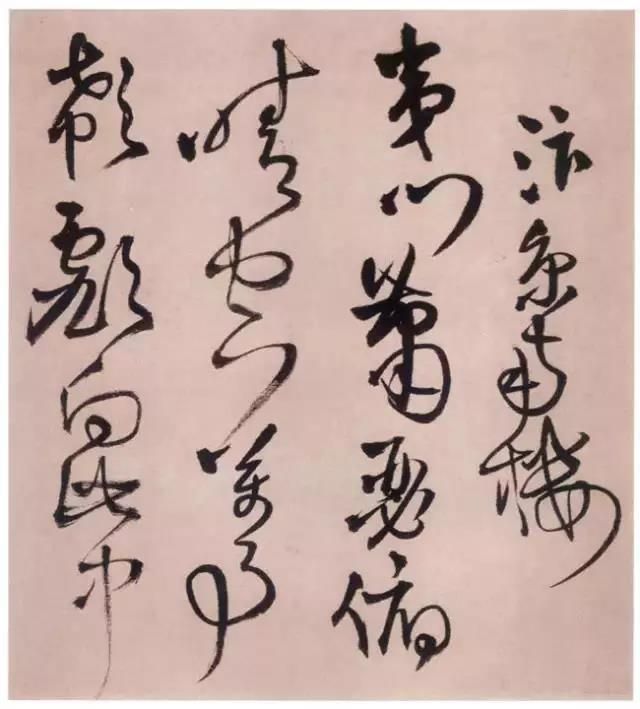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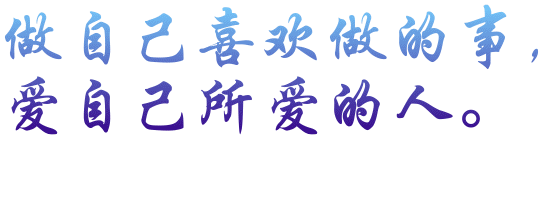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