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价值观与领导力
- 国际
- 2年前
- 186
基辛格博士谈领导力的演变
——从贵族到精英
(03)
这六位领导人从小就被灌输了中产阶级特有的价值观,包括个人自律、自我完善、慈善、爱国主义和自信。对其社会的信仰,包括对过去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法律面前平等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期望。
与他们的贵族祖先不同,这些领导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感,这激发了他们的信念,即最崇高的抱负是通过领导国家来服务于他们的同胞。他们没有把自己标榜为“世界公民”。李光耀可能在英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尼克松可能在成为总统之前对自己的旅行范围感到自豪,但两人都没有采用世界主义者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公民的特权意味着他们有责任展示自己国家特有的美德。为他们的人民服务并体现他们社会最伟大的传统是一种至高的荣誉。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很好地描述了这一价值体系在美国环境中表现出的积极影响:
不管有什么缺点,中产阶级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标准、一个共同的参照系,没有它,社会只会分裂成相互争斗的派别,正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深知的那样——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每位领导人(除了李光耀)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有虔诚的宗教背景——阿登纳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尼克松是贵格会教徒,萨达特是逊尼派穆斯林,撒切尔是卫理公会教徒。尽管这些信仰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服务于某些世俗目的:训练自我控制,反思错误,面向未来。[*]这些宗教习惯有助于灌输自我控制和着眼长远的偏好——这是这些领导人所体现的政治家风度的两个基本特征。
严酷的事实
这六个人物的精英领导有什么共同点?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
所有人都以他们的直率而闻名,并且经常讲述严酷的事实。他们没有把自己国家的命运托付给经过民意测验检验的、有针对性的言论。你认为谁输了这场战争?阿登纳毫不妥协地问他的议会同事,他们抱怨盟军在战后占领德国时强加的条款。尼克松是在政治中使用现代营销技术的先驱,他仍然以自己能够直接、坦率地掌握世界事务而不用讲稿为傲。萨达特和戴高乐擅长保持政治上的模糊性,但他们在寻求让人民朝着最终目标前进时却异常清晰生动——撒切尔也是如此。
这些领导人都有敏锐的现实感和远见卓识。平庸的领导者无法区分重大事件和普通事件;他们往往被历史无情的一面所压倒。伟大的领导者直觉地认识到治国之道的永恒要求,并在现实的诸多因素中,将那些有助于提升未来、需要提升的因素与那些必须管理、在极端情况下或许只能忍受的因素区分开来。因此,萨达特和尼克松都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了痛苦的战争,寻求克服根深蒂固的国际竞争,并开始创造性的外交。撒切尔和阿登纳发现与美国的强大联盟对他们的国家最为有利;李光耀和戴高乐选择了较低程度的结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这六个人都很大胆。即使在国内或国际条件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在国家大事上采取果断行动。撒切尔派遣了一支皇家海军特遣队从阿根廷手中收复福克兰群岛,尽管许多专家怀疑这一远征的可行性,而英国本身仍深陷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在从越南撤军完成之前,尼克松违背传统智慧,对中国进行了外交开放,并与苏联进行了军备控制谈判。
这六个人都明白孤独的重要性。萨达特在狱中加强了他的反思习惯,阿登纳在国内流亡期间在修道院也是如此。撒切尔夫人在清晨独自审阅文件时做出了一些最重要的决定。戴高乐在偏远村庄Colombey-les-Deux-églises的家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尼克松经常离开白宫,回到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戴维营或圣克莱门特。远离灯光、摄像机和日常的命令,这些领导人受益于静观和反思——尤其是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
这六位领导人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也是一个悖论——那就是他们尊重分歧。他们希望他们的人民沿着他们领导的道路前进,但他们并不争取或期待共识;争议是他们所寻求的变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1960年1月阿尔及利亚被称为“路障周”的暴乱中,我在巴黎会见法国国防机构的成员。谈到戴高乐对局势的处理,一名军官表示:“无论他何时出现,他都在分裂这个国家。”然而,最终是戴高乐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危机,让他的国家回到了对国家目标的共同看法上,就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法兰西民族摆脱了投降的耻辱一样。
类似地,没有一个领导人不会像撒切尔那样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也不会像萨达特那样与历史上的对手寻求和平,或者像李光耀那样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成功的多民族社会,而不冒犯既得利益和疏远重要的支持者。阿登纳接受了伴随德国战后占领而来的限制,这招致了他的政治批评者的责骂。戴高乐躲过了——也挑起了——无数次对抗,但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行动是平息了1968年5月将法国推向革命边缘的学生和工会抗议。萨达特殉难不仅是因为在他的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之间带来了和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用一些被认为是异端的原则来证明和平是正当的。
无论是在执政期间还是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钦佩这六位领导人或赞同他们的政策。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都面临着抵抗——通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有时是由杰出的反对派人物实施的。这就是创造历史的代价。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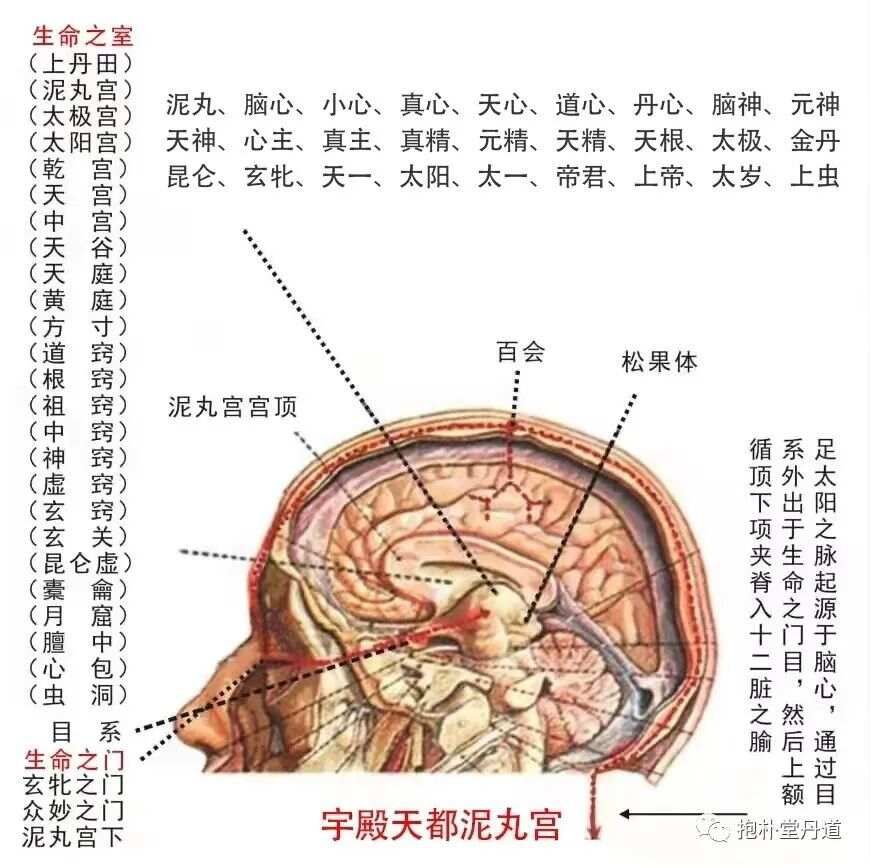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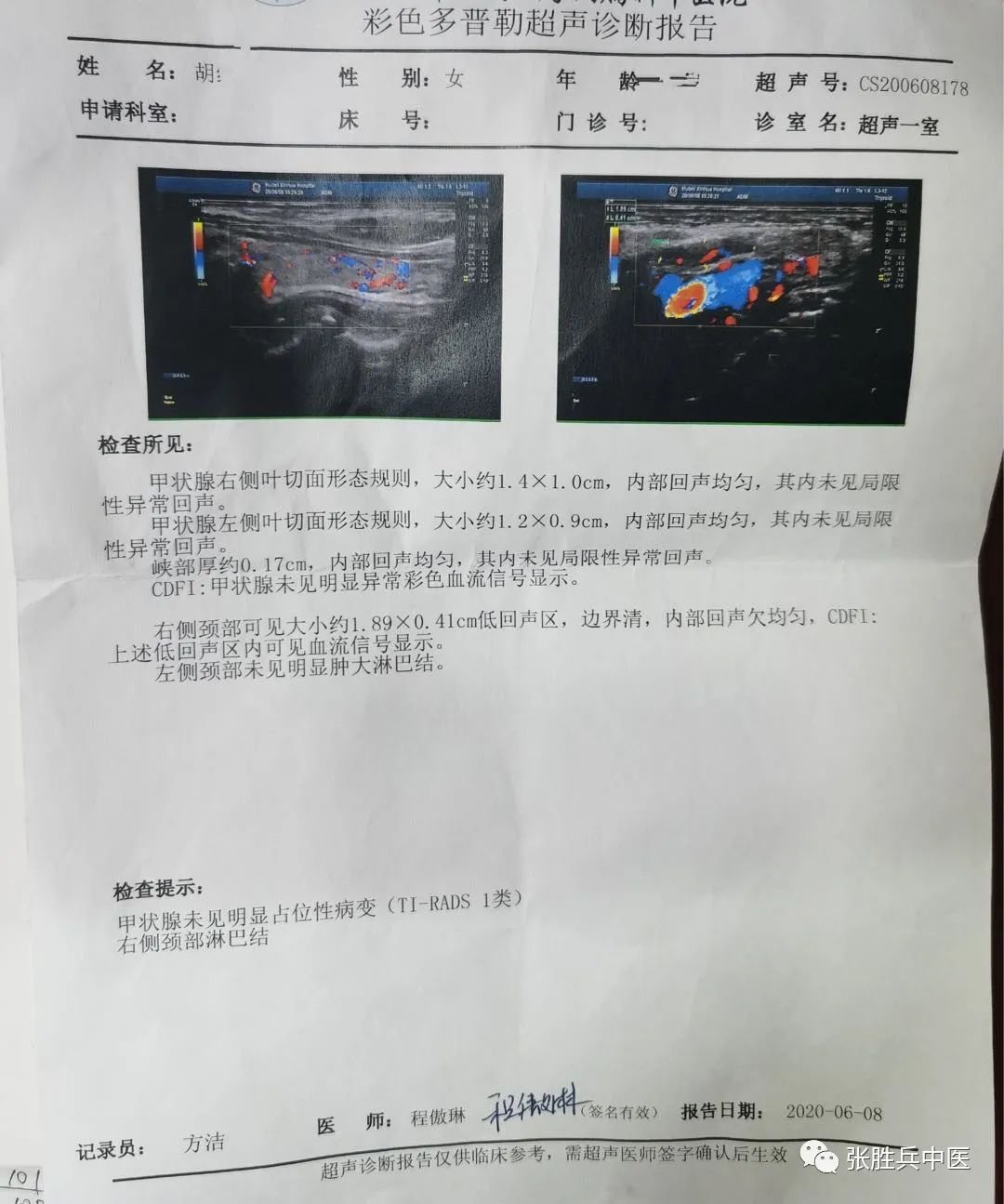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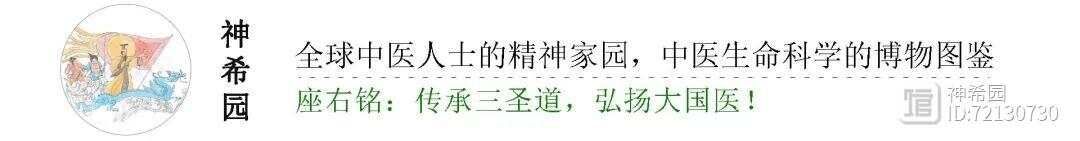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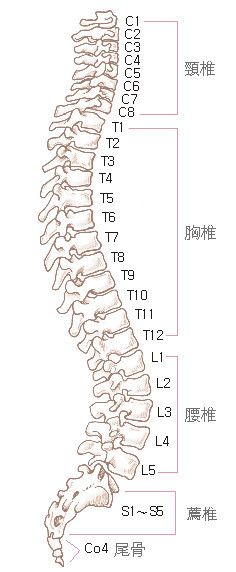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