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老法师”
- 文化
- 12个月前
- 197
为什么他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老法师”
这三年中,良师益友多有离去。先是前年,北京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丁瑜先生以95岁高龄驭鹤西游,再是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馆长吴文津先生刚过完百岁诞辰即溘然长逝,不多久又传来广东大儒王贵忱先生以94岁与世永诀,而今岁3月,沈燮元先生又以98岁疾终长眠。
我和沈燮元先生是忘年之交,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认识了,之间的互动,是因为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起。1977年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专家学者为即将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起草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三个文件。次年的3月26日至4月8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全国会议就在南京举行,而我和燮翁都与会发表了意见,那一年,他54岁,我则33岁。
结缘
198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工作在北京虎坊桥香厂路国务院信访招待所开始进行,燮翁是子部分编室的主编。我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在分编室里接触的是八百多个图书馆上报的卡片,面对各种不合规范的著录方式,也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去辨识卡片上的错误著录。燮翁和我私下里调侃说:我们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们都成了“骗子手”了。当然,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眼界更为开阔,分辨及鉴定能力也相应提高许多。
在北京《书目》编委会期间,真正看到的北京各图书馆的善本书并不多,因为只有在审查各馆报上来的善本卡片中发现问题才会就近看书解决,其中我和燮翁一起去过北京的几个图书馆,也见证了他的版本鉴定水平。但我以为印象中最深的是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看辽代刻本的《蒙求》(今藏山西应县木塔文管所),那是1974年“文革”期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的释迦佛像肚里发现的,还有一些辽代刻经。最初是由冀淑英先生与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联系,说是顾廷龙先生想看这部辽代刻本。由此,冀大姐、燮翁和我都借顾的面子,陪同顾老看到了这部极其罕见的辽代所刻之书。实际上,宋元刻本固然珍贵难得,价值千金,但当年的北图、上图、南图都有不少入藏,而辽刻只是闻其名,始终不见实物佐证,所以这次鉴赏,也是燮翁与我的福运,是一次真正的“一饱眼福”。
1981年至1987年,编委会曾借上海图书馆的206室,作为经部、史部复审、定稿的工作室,编委会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顾问潘景郑与燮翁、任光亮、我等聚于一室。能和当时国内最好的版本目录学家一起工作,是我们几位工作人员的缘分。燮翁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我以为他是编委会内除主编、副主编之外的中坚,为了工作,他在上海四年,又在北京待了四年八个月,四海为家,毫无怨言,试问这在当年甚或今天,再也找不出其他如此忘我工作之人了。
我深深地感到燮翁在工作中坚决服从编委会的安排,从不讨价还价,认真做事,克尽厥职,功成不居,为此,他获得了文化部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表彰,肯定了他在编纂《书目》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燮翁于1995年9月1日给我的信中说:“这部庞大的善本书目能经历千辛万苦后,正式出版,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付出了漫长的时光和艰巨的劳动,我想还是值得的。”燮翁参与编委会十余年的工作,也是他这数十年图书馆生涯中最有意义、最多收获,也是最能体现出他生命价值的一段经历。
除了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出勋劳外,燮翁对文献学的功业,莫过于对黄丕烈的研究。也确实是,近几年来,在中国读书界不少人都对黄丕烈的名字逐渐知晓并耳熟,这或许是因为一些媒体在采访燮翁时,都提到老人数十年中一直在研究黄丕烈,不仅辑有黄丕烈《士礼居题跋》,还有《黄丕烈年谱》的编著。黄丕烈是清代乾嘉时的一个学者型藏书家,19岁时中秀才,26岁中举人,是书林中曾经沧海的人物,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时人及后人称之为“书痴”“书淫”“书虫”“书魔”。

2019年端午,沈津去南京颐和路沈燮元宿舍拜访,95岁的沈燮元早早顶着日晒在路口迎候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图/作者提供
黄氏的一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书编目、题跋。也正因为黄氏在古书收藏、研究、传播上的贡献,他的近九百篇“黄跋”曾被后来的学者多方搜集,编辑成为《藏书题识》数种,涉及古书的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尤其是在不经意的记载中,透析出当年书之递藏、书价、学人藏家之交往,如若没有黄跋,那就是书史研究的缺欠,而不会有历史的借鉴与回忆。
燮翁四十余年如一日,每天和黄氏进行时空“对话”,要说他是黄氏的知己,或是“黄粉”,那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从来都没有问过燮翁,他是什么时候对黄丕烈发生兴趣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黄丕烈的。但是,燮翁和黄氏都是苏州人,应有地域乡邦之情,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费尽心机,多方辍拾,矻矻不倦,终于从中外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处新得他人未见之黄跋数十则,同时还纠正了旧辑本的不少讹误。1990年,87岁高龄的顾廷龙先生曾为燮翁写过一副联句,云:“复翁异代逢知己;中垒钩玄喜后生。”这是对燮翁在版本目录学、黄丕烈研究两方面恰如其分的评价。有道是知音难觅,至好不易,而燮翁实在是黄丕烈的硕交挚友、后学朋旧。
相交
1990年我离开上海定居香港,不久又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先任访问学者,后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我虽每年皆有返国之旅,但都没有机会和燮翁相见,只是通过鸿雁传书,以表思念之情。直至2002年11月,为编著《顾廷龙年谱》,我专程去了北京、上海收集材料。期间,我在结束山东大学的讲座后,乘火车直抵南京,去了南京图书馆,目的就是想见当年在一起工作的编委会副主编潘天祯先生和宫爱东副馆长、燮翁等人。这也是我离开大陆12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们,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喜形于色。
大约是十多年前吧,我返沪探亲,约好与燮翁在苏州见面。那天我坐的是早班车,35分钟后即抵苏。出站即见他在站口迎候,他知我未曾用早餐,便引我去火车站附近的西餐小店,亲点牛奶、黄油、面包、鸡蛋让我享用。我只能告诉他,在美国,我每天的早饭是泡饭加酱菜,或者方便面。他笑着说:我以为你们每天吃的都是牛奶面包,不调花头的。
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期间,曾和同事们一起举办过三次(2012年、2014年、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出席的代表均在百人左右。这三次研讨会,燮翁都参加了。燮翁那时已是当今在世的一位经冬犹茂、精爽不衰的最年高的重要版本目录学家,但他数十年来很少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更何况他没去过广州这座南方的大都市。当我邀他来中大与会时,老人说:我已退休多年,往返机票没法报销。我告之:不必担心,您尽管来,机票食宿我可协助解决。为此,我还请南图的徐忆农主任一路陪同。而第二次会上,燮翁以老苏州人的资格叙述苏州顾氏过云楼的往事。第三次与会他写了《〈嵇康集〉佚名题跋姓氏考辨》,以小见大,显见大手笔写小文章。我的中大馆同事在见到燮翁后,都认为老人确实是一位松身鹤骨、须眉交白的学者,那是因为燮翁在会议上,始终是老僧入定、正襟危坐、认真听讲的大方之家。
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江南图书馆,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所创办,后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所以它的历史早于北京的京师图书馆。从早期的缪荃孙、柳诒徵,再到钱亚新、汪长炳,都是俊杰翘楚般的人物。而燮翁则是另类的有识之士,他退休前曾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官职,即使在任上,也没小官架子,从不钻营取巧,也无虚荣歆羡之心,而是把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您也别说,他是性情中人,自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忆当年和他接触,还只是感到他的博学、随和、平易,是个无日不读书的学者文人。
他在南图工作了五十余年,告老归休后,却退而不息,坚持每天风雨无阻地去到南图古籍部“打卡”,不仅日日伏于几案,潜心典籍,还不时利用他广博的知识面为读者排扰解难,指点迷津,为他人作嫁衣裳。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早已忘却自己的年龄,他不是什么大师、宗匠,只是一位平凡的普通的文弱老者,即使走在繁华大街上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但正是书生本色却成就了他成为图书馆学界、文献学界中的芝兰玉树、南金东箭,也是南图专业工作人员的骄傲和典范。
我和燮翁交往四十余年,互相信任,彼此无忌,所以在聊天或邮件中也会臧否人物,品评图书。我有时也会就某种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征求他的意见,印象最深的是某教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他连说了两句 “不来事”“不来事”(苏州话,意为不行、不行)。燮翁此说是指书中谬误多多,但没有说此书的要害,有剽窃日本学者著作之嫌。另一件事,是某君胆大妄为,直接剽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成果,这使燮翁大动肝火,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怒不可遏的模样。当然,偷盗者并未参与《书目》编委会的任何工作,却利用没有被收回的《征求意见稿》(油印本),私自交北京某出版单位出版,骗取名和利。燮翁愤然说:这种人没有自信,却窃取我们辛劳工作18年的劳动硕果。他也对我说,如正副主编顾廷龙及冀淑英、潘天祯三先生在世,一定会被气得吐血。
燮翁生于1924年,大我21岁,他1955年进入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我于1960年拜师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习流略之学,因此,燮翁是我的前辈。但是对于顾师来说,燮翁又是晚辈了。顾师以95岁高龄去世,他的墓即在苏州七子山墓地。在李军兄的安排下,我和燮翁联袂拜祭过三次。第一次去是2017年5月,如果说我跪叩先师是天经地义之礼,但令我感动的是,燮翁也要跪拜。我说:您就不要跪了,鞠三个躬吧。他说:不行,顾老对我有恩,提携过我,我是一定要跪拜的。我知道,那是指1948年,燮翁从无锡国专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顾师留他在合众图书馆任干事之职,时间约为半年。一位九十四岁的老人,腿脚不便,平时行动缓慢,走路都谨慎小心,却坚持要做如此这般“大动作”。当时我侍立在旁,礼毕,我赶紧扶他慢慢起立,只见他喘个不停,所以就在旁边较宽的石栏坐下休息。次年5月,我们又结伴去苏州十梓街“顾廷龙故居”,还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永诀
2011年2月,我自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退休后,每年都会返国两次,于是也有机会在上海、苏州、南京和燮翁见面。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南京。那是2019年端午节前后,我应南京艺术学院之邀,前去作了两次讲座,期间约好燮翁,在颐和路他的宿舍见面。那天早上我偕小友王宇博士同去,刚转到颐和路口,就看到老人顶着日晒,早早站在路边等候我们,毕竟是耆宿大贤之人,这让我们十分不安。燮翁所居本为南京图书馆馆长汪长炳先生所有,几经变迁,二楼已成工作人员宿舍。由此想起,过去每次我通过越洋电话问候燮翁起居,都是通过汪氏后人传呼而成。进入室内,还没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引领我去参观二楼厕所旁的新装浴缸,我很难想象燮翁这几十年来在炎炎夏日中,是如何度过洗澡这一关的。

2019年, (从左至右)马骥(苏州收藏家)、沈燮元、陈鸿森( 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时为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和沈津在苏州聚会。图/作者提供
燮翁是一位平凡的读书人,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业余爱好无他,就是喜欢书,我看他在苏州居处二楼的书房,各式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图书,以及相关的参考书、工具书,排放整齐,即使小部分的港台此类出版物,也是他通过相应的渠道多方访得。而颐和路宿舍不大的房间整理得还算干净,但最显眼的还是堆得满处的书,床边小几、地板上都是。
那一次闲聊最多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过程中的人和事,我们都感到这个题目没有人做,而参与此目编纂全过程的健在者当时仅有燮翁、丁瑜(前年仙逝)、任光亮和我。本想再找时间约任兄在沪或苏州见面,好好聊聊,但没想到之后疫情肆虐,我也无法返沪。然而我们之间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次永远的诀别。
燮翁藏书中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二金蝶堂印存》,这是清代篆刻大家赵之谦的铁笔,燮翁收集了赵氏印文八十余枚,辑成印谱,精装成帙。后来他请先师顾廷龙先生题诗于上,诗云:“丛残掇拾见奇珍,金蝶馀痕检点新。明眼多君能事在,琳琅锦笈伴昏晨。长年精力勤书府,诸子百家乐有馀。剪取金陵山水影,还将画意补新图。”此《印存》是燮翁宝爱之物,轻易不肯示人。顾师挥毫为之锦上添花,也是佳话一则。
除了书之外,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或许还有嗜酒若燮翁者。还记得30年前,同道们互传燮翁喜酒,但不能多饮,每次一小杯,多则要手舞足蹈起来。这是燮翁认可之说。犹记得在香厂路期间,某个星期天的傍晚,丁瑜来接顾廷龙先生、燮翁和我去延年胡同他家吃饺子,还配有酒菜,燮翁多喝了一小盅,所以回程话特多,一路上说个不停,也因此,我说他是酒精起作用了。直到晚年,他仍保持昔年旧习,但并不贪杯,或许小酒也是他长寿之一招。
燮翁不常用毛笔写字,偶有所作,乃是应友朋之请。他的书法作品,我仅有一幅。那是2017年由李军兄安排,我和燮翁约在苏州怡园茶室见面,聊天时,我提请燮翁为我写一幅字,谁知他接着说,那你也要为我写一幅,我们交换。三个月后,我们又在茶室叙旧,他从羽绒服内里的口袋里取出折叠得像手机般大小的纸递给我,也没有信封。燮翁的书法是没有章法可寻的,没有刻意,没有做作,一气呵成,笔到为止,细看则多了些稚意。我以为这和他平常使用的圆珠笔或钢笔写的字形差不了多少,只是使用的笔具不同而已。宋人程明道说“非欲字好,即此是学”。所以燮翁的字是文人学者体,是无欲品自高的境界。
燮翁是今年2月14日入住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后又转至江苏省人民医院本部,共住了45天。他住院期间,王宇博士时去探望,每次都借用她的手机让我与燮翁视频。最初他还意识清楚,居然聊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谢正光兄,谢退休前为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历史系教授。但之后的几次视频令人担忧,老人能认识我,但已说不出话。再后来则无力睁眼了。
对于老人的过世,家属及时去探望的友人都有预感。这不仅是3月下旬医生开具的两次病危通知单,而且老人依靠鼻饲等器具进入的营养液及较长时间的昏睡状况也令人不安。燮翁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天的日历定格在3月29日上午8时22分,这距他的九九大寿(他生于1924年6月19日),只有82天。
四年前,我曾为燮翁的《沈燮元文集》作序。序文的最后一段是:“燮翁高龄,今年九十有五,已踰鲐背之年。更难得的是他康健如昔,不时往来苏宁两地。”“燮翁在图书馆学界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地位,是当仁不让的老法师级人物,无人可出其上,其阅历之资之深,也无人能望其项背。”“很多见过燮翁的朋友,都为老人的健康表现出欣羡之情。我亦以为待到山花烂漫时,老人期颐之年,约上一班忘年之交,好好作一次畅怀痛饮。”如今只有叹之、憾之。
逝者已矣,生者坚强。燮翁走了,津不能返国见最后一面,只得请友人代置花圈,上书“曾经唐文治茹经堂门下客,今为黄丕烈士礼居忘年交”。昔日老友的音容笑貌再也见不到了,也听不到他那夹杂着上海话的侬侬吴语。燮翁留给世人的是鸿儒、耆宿的影像,以及那淡泊名利的本色,而留给我的不仅是厚厚一叠手札和墨宝,还有那不尽的回忆和哀思。或许珍惜已拥有的人生,继续奋发向前,才是对老人最好的祭奠。俱往矣!如若天堂里真有图书馆的设置,那或许是燮翁的归宿。
(作者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原主任,现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发于2023.4.24总第108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我的忘年之交沈燮元先生
作者:沈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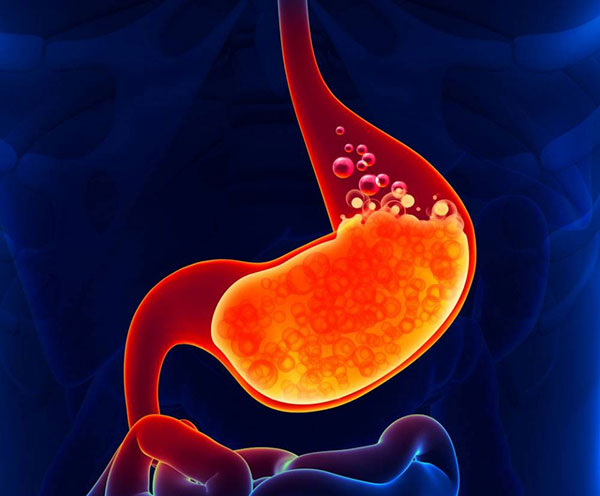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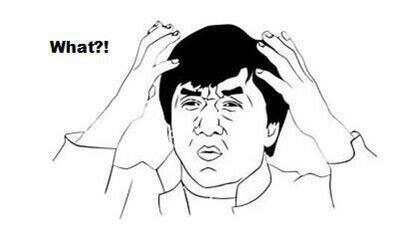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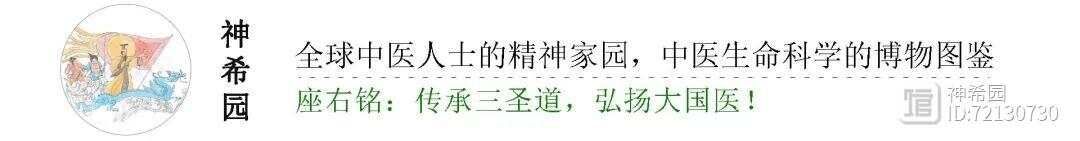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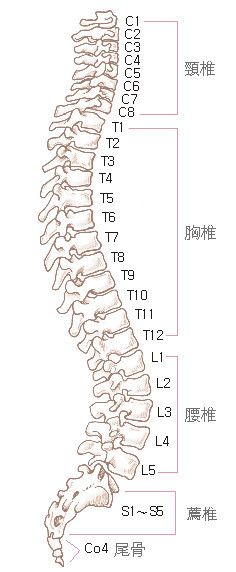








有话要说...